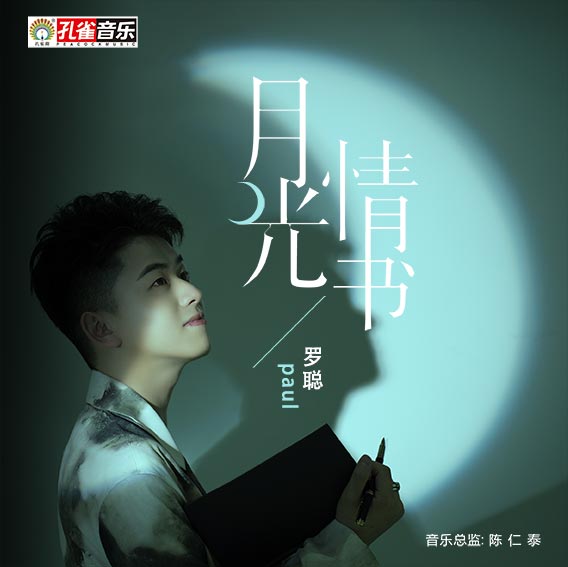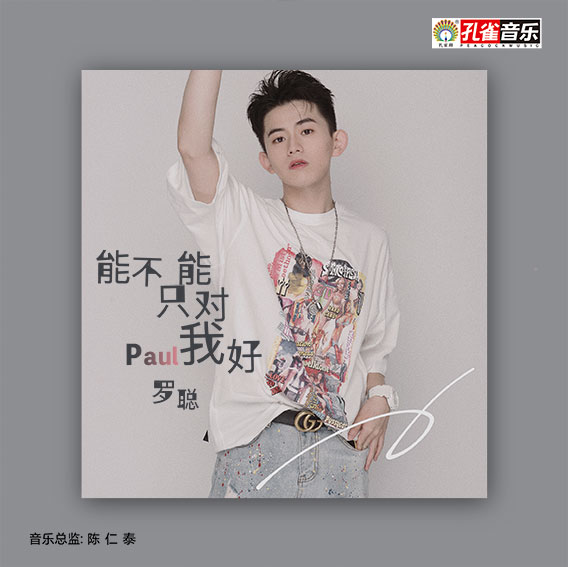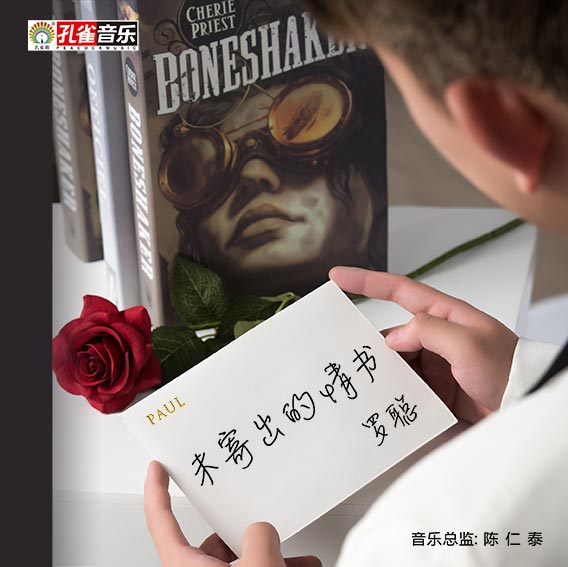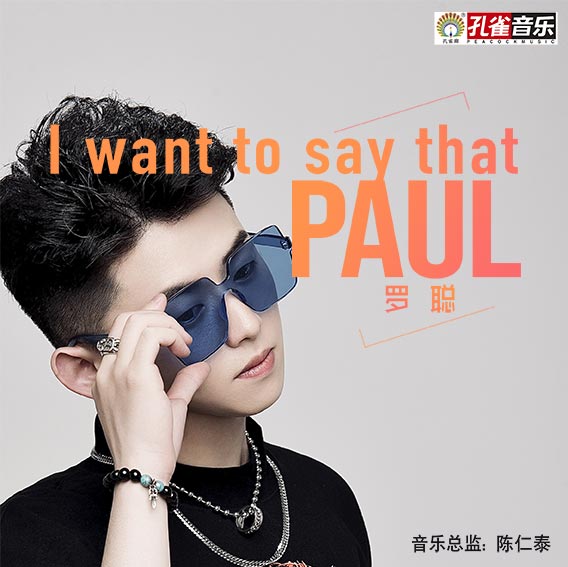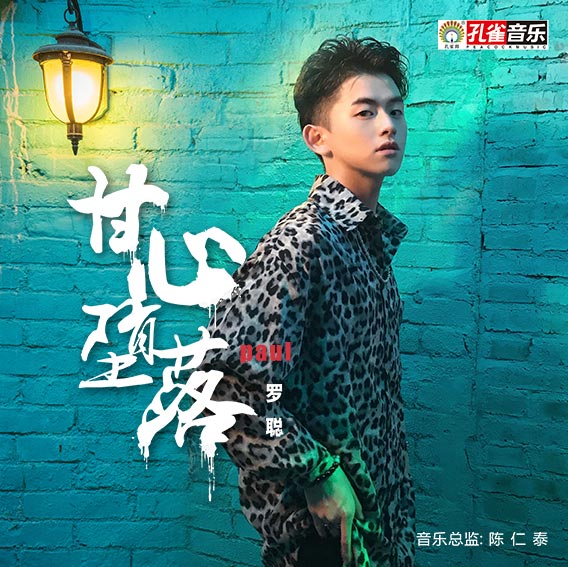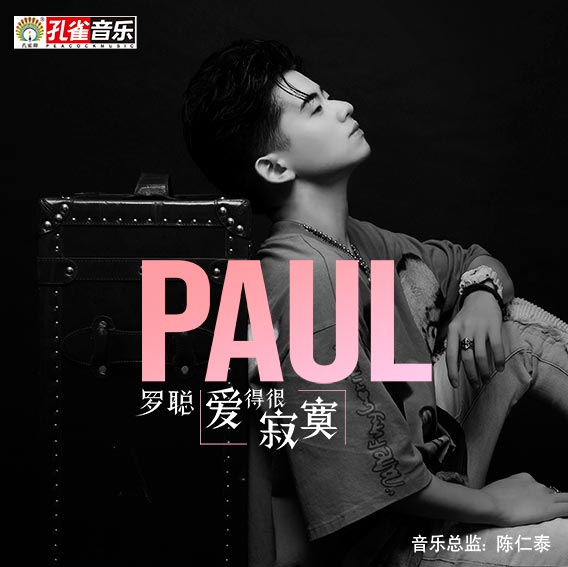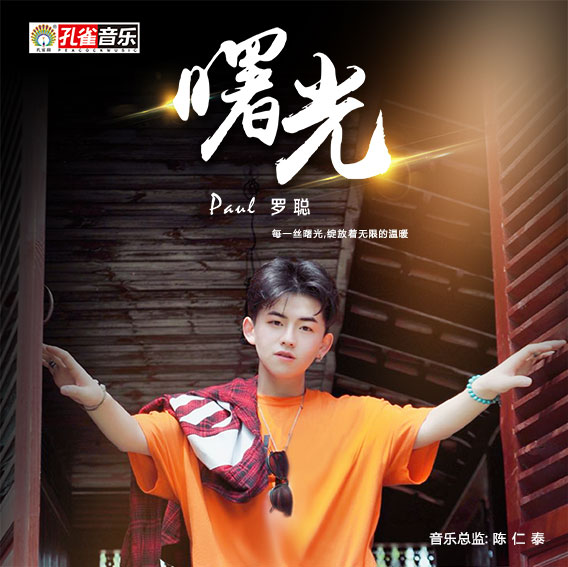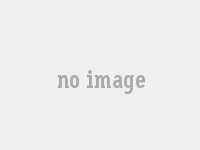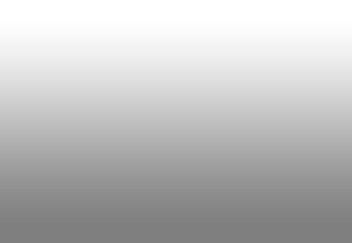

专辑名称:做梦的孩子
所属歌手:罗聪
专辑类型:流行
发行公司:孔雀廊
把池塘折成月亮,把童年折进梦里
歌曲一开口就是“儿时门前的池塘/已经瘦的像一弯月亮”。一个“瘦”字,把三十年的时间蒸发成几缕水汽,也把童年的丰沛与现实的干涸一并托出。最动人的是,它们不是被“回忆”出来的,而是被“折叠”出来的——像一张反复摩挲的糖纸,颜色还在,只是多了无法抚平的皱褶。
“多想还是那个睡着就会做梦的孩子”——这句看似平常,实则是一次“逆向飞行”。它把成年人的沉重肉身留在地面,只让灵魂沿着旧轨迹返航:
这是一种对“效率社会”的软抵抗:不控诉,只撒娇;不批判,只贪玩。童年之所以发光,恰在于它无法被任何KPI衡量。
歌曲结束,没有大合唱式的高潮,只留下一句“从前重复的游戏原来比现在有意思”。它像一颗玻璃球,在耳边轻轻滚动——那其实是我们自己心跳的回声。
整首歌里,罗聪的嗓音始终保持着克制的温度,没有刻意煽情,却让“时光匆忙成长/童年被遗忘”的怅惘自然流淌。他用声音搭建起“现实”与“梦境”的桥梁,唱回忆时带着清晰的画面感,唱渴望时又添上几分缥缈的向往,最终让“在梦里当一回孩子王”的心声变得真实可触,也让每一个在成长中失落过的人,都能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共鸣。
《做梦的孩子》最珍贵的地方,是它不提供“治愈”,只提供一次“透气的缝隙”。当耳机摘下,你依然要赶地铁、回邮件、做PPT,但掌心或许还留着那张皱巴巴的糖纸——证明你刚刚偷偷回了一趟故乡,把池塘折成了月亮。